关联公司混同用工模式下劳动关系确认的法律解析与实践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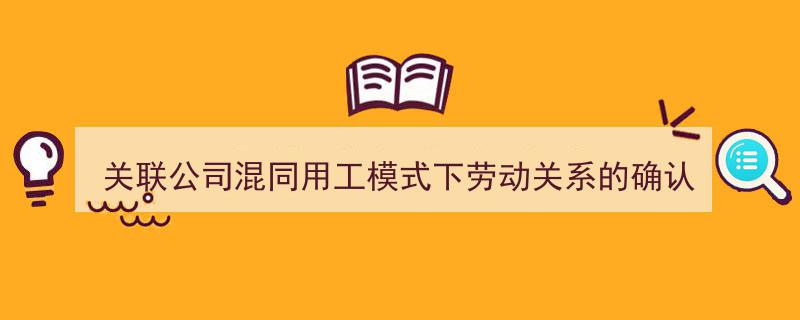
在关联公司混同用工模式下,劳动关系的确认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劳动法、公司法、合同法等多个法律领域。以下是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方法:
### 1. 劳动关系的定义
首先,需要明确劳动关系的定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劳动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基于劳动者提供劳动,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合同关系。
### 2. 关联公司混同用工模式
关联公司混同用工模式通常指的是两个或多个关联公司(即具有股权关系或其他利益关联的公司)在用工上相互混同,使得劳动者难以区分具体用工主体。
### 3. 确认劳动关系的原则
#### a. 实际用工主体
首先应确定实际用工主体。如果劳动者在实质上是由某一公司实际管理和使用,那么该公司的法律地位应当被认定为劳动关系。
#### b. 劳动合同签订
查看劳动合同的签订主体。如果劳动合同是由关联公司之一签订,并且劳动者实际在该公司工作,那么该公司的法律地位应当被认定为劳动关系。
#### c. 劳动报酬支付
劳动报酬的支付情况也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如果劳动报酬是由某一公司支付,那么该公司的法律地位应当被认定为劳动关系。
#### d. 工作地点与工作内容
劳动者实际工作地点和工作内容也是判断劳动关系的重要依据。如果劳动者在某一公司实际工作,且工作内容与该公司业务相关,那么该公司的法律地位应当被
相关内容:
——郑某诉甲科技公司劳动争议案【基本案情】2021年5月12日,郑某驾驶涉案重型厢式货车与案外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受伤,此后未再提供劳动。甲科技公司股东兼监事张某1为郑某垫付医药费107500元。郑某称经人介绍于2021年3月1日入职甲科技公司,岗位为运输司机,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保,丁科技公司和丙科技公司代发工资,入职系与队长王某商谈,从王某处接手涉案车辆,平时接受王某管理,王某系某供应链公司调度,某供应链公司的现法定代表人与甲科技公司前法定代表人均为张某。甲科技公司否认与郑某存在劳动关系,表示其只是涉案车辆的登记车主,该车辆已于2020年出租给乙科技公司,乙科技公司与丁科技公司、丙科技公司分别签订了《外包项目平台综合服务协议》《服务合同》,通过两公司运营的平台招聘司机,由两公司承揽业务,郑某与丁科技公司、丙科技公司签订协议,从平台注册后接单。2020年8月7日至2021年11月3日张某为甲科技公司股东兼法定代表人,2020年8月7日至今张某1为甲科技公司股东、监事;乙科技公司成立于2019年3月20日,2019年3月20日至2022年8月25日张某担任法定代表人。乙科技公司自2021年3月10日起为郑某投保雇主责任险。 【案件焦点】甲科技公司与郑某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法院裁判要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判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以实质要件为判断标准,核心要素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形成实际控制,双方形成财产上、人身上的从属性关系。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可知,郑某驾驶甲科技公司车辆从事运输工作,根据平台派单情况显示郑某驾驶车辆运输的承运商名称为甲科技公司,虽甲科技公司主张将车辆出租给乙科技公司,但甲科技公司与乙科技公司系关联公司,郑某从事的工作实际为甲科技公司业务的一部分;根据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王某向郑某发送定位、安排工作等内容能够认定郑某接受王某管理,王某自称系某供应链公司员工,能够认定郑某接受某供应链公司调度,某供应链公司对郑某进行管理,而某供应链公司与甲科技公司为关联公司;郑某的工资虽名义上由丁科技公司、丙科技公司代发,但实际上支付主体为甲科技公司的关联公司乙科技公司。以上特征均显示甲科技公司与郑某之间形成财产上、人身上的从属性关系,符合成立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综上,甲科技公司虽然主张与郑某不存在劳动关系,但与查明事实相悖,故法院不予采信。法院认定甲科技公司与郑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甲科技公司作为劳动关系中负有管理责任的一方,应对劳动者入职时间、工作年限承担举证义务,其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结合在案证据,法院对于郑某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予以采信,确认双方2021年3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郑某与甲科技公司自2021年3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甲科技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后语】关联公司,作为一种更具规模性和竞争性的企业组织型态,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实践中,部分关联公司为创新业务模式或规避用工风险往往将劳动关系诸要素打散,劳动者分别与多家公司存在一定关联,但又找不到确定、完整的用工主体,出现纠纷后关联公司之间相互推诿责任。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混同用工案件时,面临用工主体多元、用工结构复杂、劳动关系认定困难等现实挑战。司法实践中,关联公司混同用工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一套人马,多块牌子”,混淆用工。实践中多家关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等为同一人或具有亲属关系,办公场所、人事财务、业务内容等高度混同,往往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故意混淆用工,劳动者亦无法知晓自己到底属于哪一家单位。二是采用出租合同、承包合同等形式,隐蔽用工。实践中部分关联公司在发生劳动纠纷时,往往主张相应场地、设备、业务等已出租、承包给第三人经营,劳动者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等。用人单位表面上与关联公司之间签订出租合同、承包合同等普通民事合同,但对劳动者的招录聘用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过程等进行实际管理,导致劳动关系认定、劳动者工龄计算、社会保险缴纳等均存在不同隐患。三是不断变换主体,交替用工。实践中部分集团公司通过变换不同的签约主体和劳动者签署劳动合同,劳动者的工作内容、管理隶属等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劳动合同、工资发放、社保缴纳等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关联公司交替轮流用工,以此规避支付经济补偿、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法律义务。关联公司混同用工情形下,相关用工事实查明困难,劳动关系扑朔迷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劳动法的立法宗旨,而确认劳动关系是各项劳动权益保障的起点。实践中应当坚持事实优先原则,无论存在多少主体,都应根据劳动合同签订、用工管理事实等作出综合判断,必要时可以尊重劳动者的选择权。从程序上而言,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劳动者申请或者依职权追加其他关联公司参加诉讼,以查清用工事实,减少劳动者诉累。本案中,郑某驾驶甲科技公司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为认定工伤无奈寻求确认劳动关系。甲科技公司辩称已将车辆出租给乙科技公司,而从在案证据来看,两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乙科技公司则辩称属于平台用工,和郑某不存在劳动关系,用工链条进一步拉长。一审法院依法通知某供应链公司、丁科技公司、丙科技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进一步查清事实。
【案件焦点】甲科技公司与郑某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法院裁判要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判断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应以实质要件为判断标准,核心要素是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形成实际控制,双方形成财产上、人身上的从属性关系。根据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及陈述可知,郑某驾驶甲科技公司车辆从事运输工作,根据平台派单情况显示郑某驾驶车辆运输的承运商名称为甲科技公司,虽甲科技公司主张将车辆出租给乙科技公司,但甲科技公司与乙科技公司系关联公司,郑某从事的工作实际为甲科技公司业务的一部分;根据微信群聊天记录,显示王某向郑某发送定位、安排工作等内容能够认定郑某接受王某管理,王某自称系某供应链公司员工,能够认定郑某接受某供应链公司调度,某供应链公司对郑某进行管理,而某供应链公司与甲科技公司为关联公司;郑某的工资虽名义上由丁科技公司、丙科技公司代发,但实际上支付主体为甲科技公司的关联公司乙科技公司。以上特征均显示甲科技公司与郑某之间形成财产上、人身上的从属性关系,符合成立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综上,甲科技公司虽然主张与郑某不存在劳动关系,但与查明事实相悖,故法院不予采信。法院认定甲科技公司与郑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甲科技公司作为劳动关系中负有管理责任的一方,应对劳动者入职时间、工作年限承担举证义务,其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应承担不利后果。结合在案证据,法院对于郑某主张的劳动关系存续期间予以采信,确认双方2021年3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确认郑某与甲科技公司自2021年3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存在劳动关系。甲科技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后语】关联公司,作为一种更具规模性和竞争性的企业组织型态,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实践中,部分关联公司为创新业务模式或规避用工风险往往将劳动关系诸要素打散,劳动者分别与多家公司存在一定关联,但又找不到确定、完整的用工主体,出现纠纷后关联公司之间相互推诿责任。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混同用工案件时,面临用工主体多元、用工结构复杂、劳动关系认定困难等现实挑战。司法实践中,关联公司混同用工案件,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一套人马,多块牌子”,混淆用工。实践中多家关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等为同一人或具有亲属关系,办公场所、人事财务、业务内容等高度混同,往往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故意混淆用工,劳动者亦无法知晓自己到底属于哪一家单位。二是采用出租合同、承包合同等形式,隐蔽用工。实践中部分关联公司在发生劳动纠纷时,往往主张相应场地、设备、业务等已出租、承包给第三人经营,劳动者与第三人存在劳动关系等。用人单位表面上与关联公司之间签订出租合同、承包合同等普通民事合同,但对劳动者的招录聘用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工作过程等进行实际管理,导致劳动关系认定、劳动者工龄计算、社会保险缴纳等均存在不同隐患。三是不断变换主体,交替用工。实践中部分集团公司通过变换不同的签约主体和劳动者签署劳动合同,劳动者的工作内容、管理隶属等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但劳动合同、工资发放、社保缴纳等可能分布在不同的子公司或分公司。关联公司交替轮流用工,以此规避支付经济补偿、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法律义务。关联公司混同用工情形下,相关用工事实查明困难,劳动关系扑朔迷离。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劳动法的立法宗旨,而确认劳动关系是各项劳动权益保障的起点。实践中应当坚持事实优先原则,无论存在多少主体,都应根据劳动合同签订、用工管理事实等作出综合判断,必要时可以尊重劳动者的选择权。从程序上而言,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劳动者申请或者依职权追加其他关联公司参加诉讼,以查清用工事实,减少劳动者诉累。本案中,郑某驾驶甲科技公司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为认定工伤无奈寻求确认劳动关系。甲科技公司辩称已将车辆出租给乙科技公司,而从在案证据来看,两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乙科技公司则辩称属于平台用工,和郑某不存在劳动关系,用工链条进一步拉长。一审法院依法通知某供应链公司、丁科技公司、丙科技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进一步查清事实。从实体上而言,多家关联公司混同用工,劳动关系诸要素分散、交叉的情形下,可以将招录聘用、日常管理、绩效考核、工资支付、保险缴纳等综合作为判断劳动关系的因素。一般而言,(1)订立劳动合同的,可以按照劳动合同确立劳动关系;(2)未订立劳动合同的,以有关联关系的用人单位发放工资、缴纳社会保险、工作地点、工作内容、日常管理等与劳动合同履行相关的要素综合进行判断;(3)难以厘清与哪家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的,因为造成劳动关系混同的过错在于多家关联公司,从诉讼经济角度考虑,也可以依据劳动者的选择进行确认。本案中,甲科技公司系车辆所有人,为郑某垫付医药费,某供应链公司对郑某进行日常管理,乙科技公司为郑某投保了雇主责任险,三家公司存在关联关系,均未与郑某签订劳动合同,法院依据郑某的选择确认与甲科技公司存在劳动关系。此外,本案中乙科技公司与丁科技公司、丙科技公司签订相关协议,由后者与郑某签订相关协议、代发工资。用人单位招录劳动者后,要求劳动者在互联网平台注册为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等,并通过互联网平台代发工资等方式规避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依据实际用工情况进行认定,以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