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中纪委划出党员干部营利活动“红线”,明确纪法边界,严防利益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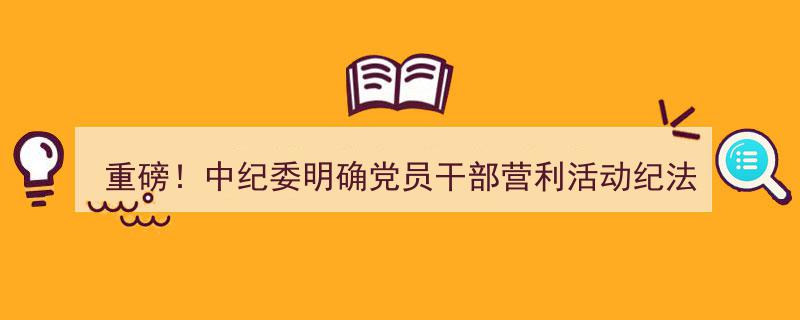
根据中纪委的明确,党员干部在营利活动中的纪法边界如下:
1. 党员干部不得从事营利性活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行为:
(1)个人或通过他人以投资、融资、担保、委托、承包、租赁、经营、转让、出售等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营利性活动;
(2)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者他人从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3)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者他人从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4)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者他人从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5)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本人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者他人从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2. 党员干部在以下情况下,可以从事营利性活动:
(1)在履行职责范围内,为国家和集体利益服务,不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2)通过合法途径,参与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的经营活动,但不得利用
相关内容:
在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的背景下,党员干部违规从事营利活动的行为界定一直是纪律审查中的焦点议题。近期,中纪委从办案实践出发,对党员干部营利活动的纪、法、罪认定标准作出系统性梳理,通过厘清三类行为边界,为精准执纪执法提供了清晰指引。
一、违纪认定:从"市场行为"到"身份限制"的双重考量
营利活动本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行为,既包括经商办企业等直接投资,也涵盖股票、基金等间接投资。但对党员干部而言,判断是否违纪的核心在于是否"违反有关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属于违反廉洁纪律的情形,相关规定散见于《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等多部制度文件中。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营利活动本身符合市场规则,若行为方式不当仍可能触碰其他纪律红线。例如党员干部炒股未按要求报告个人事项,可能违反组织纪律;在工作时间参与营利活动并造成不良影响,则可能违反工作纪律。这种"行为合规但程序违规"的情形,正成为近年来监督检查的重点。
二、纪法衔接:不同主体身份的差异化认定逻辑
违纪与职务违法的认定既各有依据,又存在内在统一性。党纪党规聚焦党员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要求,而《政务处分法》等法规则实现对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在具体认定中,主体身份直接影响市场准入限制:
- 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被严格禁止经商办企业;
- 国企领导干部需遵守投资入股竞业禁止规定;
-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则需区分管理岗与专业技术岗——例如科研人员经批准可离岗创业,但管理岗领导人员仍受任职限制。
这种差异化认定体现了"精准执纪"的原则。对兼具党员身份的公职人员,若违纪行为需给予重处分,需同步进行政务处分;对非党员公职人员,则需依据其具体身份对应的法规审慎研判,避免出现监督盲区。
三、罪与非罪:投资型受贿的"市场定价"与"权力定价"分野
在违纪与职务犯罪的交织地带,投资型受贿的定性尤为关键。此类行为往往以"实际出资"为表象,通过隐名持股、借贷协议等方式掩盖权钱交易本质。区分违纪与受贿的核心在于收益性质:
- 若收益源于市场正常交易,即使主体身份违规,仍属违纪范畴;
- 若收益明显高于市场公允价格,且与"利用职务之便谋利"形成对价,则构成受贿犯罪。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非公开市场中的"突击入股""定向增发"等新型投资行为,中纪委特别指出:若领导干部利用职权突破准入限制、在封闭期内违规退出并获取巨额收益,实质是"权力套利",建议纳入刑法评价。这一表态对金融领域反腐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从办案实践看,违规营利行为正呈现"手段隐蔽化、类型复杂化"的特点,此次中纪委对纪法罪边界的重新界定,既是对"越往后越严"信号的强化,也为精准运用"四种形态"提供了操作指南。随着这一标准的落地,党员干部的行为边界将更加清晰,政治生态与市场秩序的协同净化也将迈向更深层次。
